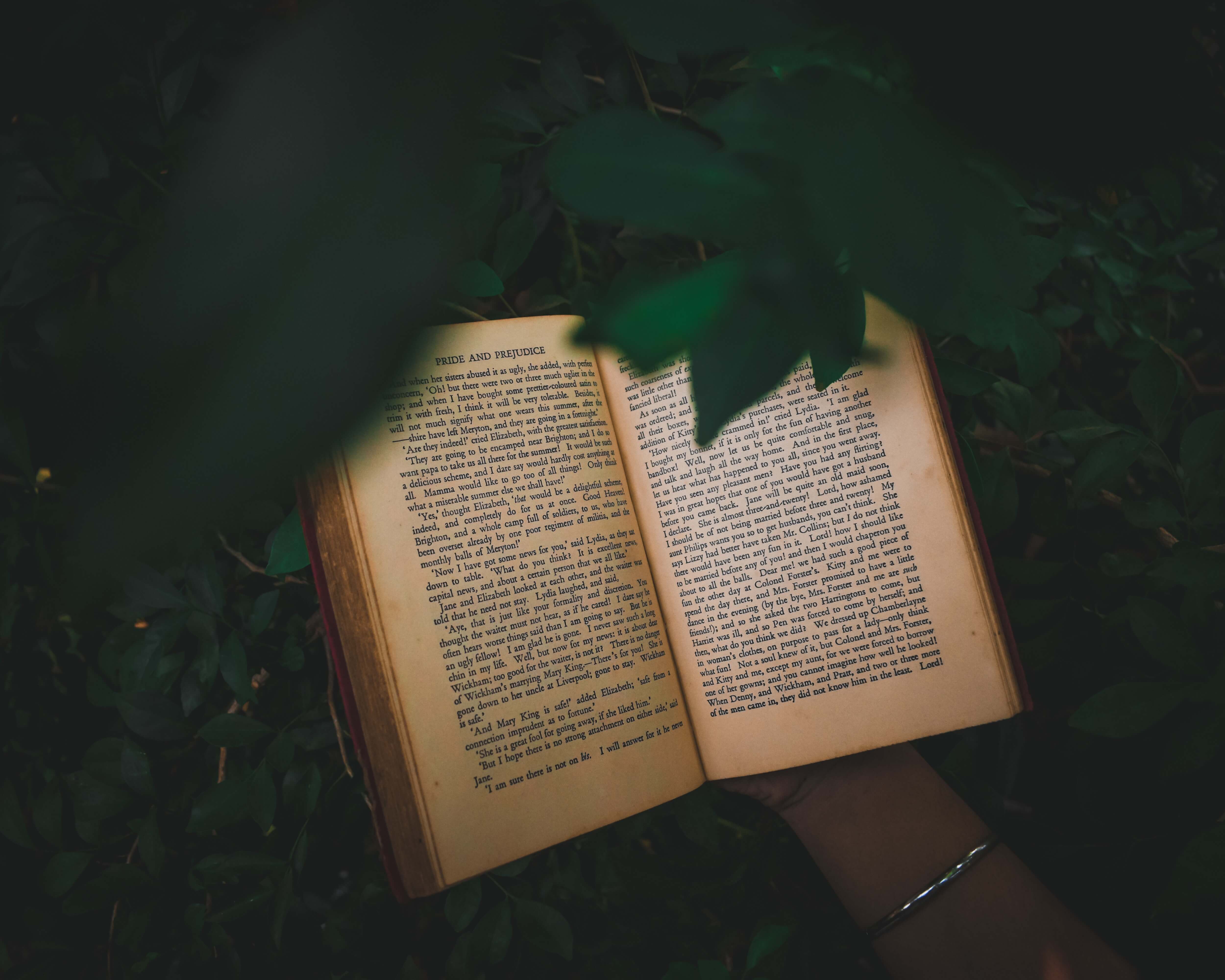此外,現時土地供應的資料不全,當局每年只向立法會交代造地「流水帳」,不講需求,只講政府造了多少地,民間根本無從知悉缺口。 據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立之初,政府只提供至2046年土地供應為3600公頃、需求為4800公頃的兩組數字。 經小組力爭,政府才提供土地缺口的分項數字,包括房屋、經濟及基建用地,以及短缺的年期(短中期及中長期)。 小組有成員指出,現時政府的造地機制出了大問題,不單規劃及審批慢,而且漏洞百出。
他舉例說,當年沙田第一城是由政府畫出一個海床,讓四大發展商按政府規劃去填海建屋。 他又指特首林鄭月娥稱,「明日大嶼」填海計劃要用14年才可住人,但當年港督衛奕信1989年提出的「玫瑰園計劃」,西九填海、青馬大橋及搬機場也只用了10年,何解? 又例如赤鱲角機場第三條跑道,由行會拍板至填完,只需5年。 如果能夠走出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不難發現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關乎所有市民,並非你我之間的糾紛;而且其中有不同的紓解問題方法,可以兼容並蓄,發揮更大的效果。
土地大辯論: 土地大辯論的幾個問題
然而,有委員認為,現時政府使用發展局轄下的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去處理有關問題,透明度不足,靠專業團體推舉代表參與,結果有不少是發展商的代表或相關人士。 土地不足問題刻不容緩,特首甫上任成立的土地供應小組(小組),就不同增加土地供應選項進行五個月的公眾諮詢,並提交最終報告。 我樂見政府從善如流,全盤接納報告,將按小組報告的建議增加土地供應,解決本港的房屋土地問題。
當時土供組指球場餘下140公頃的土地仍可繼續舉辦國際高球賽事及球員培訓,已平衡土地及體育發展需要。 小組又指,局部方案若涉及高密度發展,將集中於舊場目前作停車場的部份,對球場生態及保育功能影響較少。 但政府於2020年10月又公布,會把相關土地續租給香港哥爾夫球會3年,每年收取1元象徵式租金,當時政府稱屬「特別過渡安排」,租約今年8月屆滿。
土地大辯論: 填海造地是慣常做法
據行業人士透露,就算大陸發展商成功投地,也要靠本地龍頭替其「打通脈絡」。 相關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且十分官僚,批核需時,要求複雜。 本地法規上亦有「陷阱」是不足為外人道,要熟行的人「指點迷津」。 本地承建商、材料供應商都與本地地產商關係極佳,連本地工人的數量亦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雖然被譽為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但幾大本地發展商都形成了自然的寡頭壟斷,駸駸然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 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就算大陸地產龍頭來港發展,亦要靠土地財閥做其「盲公竹」。
從政者往往可以開天殺價,要求政府接受自己的方案,但最終良好政治終歸是妥協的藝術,我們也要接受現實。 以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為例,收回整個球場發展房屋不是新鮮事,不少團體早在數年前提出,但時任政府寸土不動,置若罔聞。 在小組的報告中,建議收回部分球場發展房屋,正是反映民意的結果。 如果從政者硬要聚焦收回整個球場,不取中庸之道,只變成姿態大於實際,短期內不會取得任何實質成果。 在另一個具爭議性的填海議題上,我希望社會也可回歸理性思考,放眼未來。
土地大辯論: 發展內河碼頭
有委員更直言,香港弄致今時今日如斯田地,實為「人禍」。 「我現在對鏡頭說,無任歡迎任何政府部門前來北區考察。」侯志強提出,新界仍有大量土地有待開發,促請政府實地考察。 他強調,政府有足夠的土地,滿足工業和房屋等各種需求,「鄉村範圍外面,其實仍有大量土地,足夠發展多兩個香港」。 侯志強認為,政府與其考慮填海或開發郊野公園,應先善用手頭上現成的土地資源,從詳規劃,擺脫過往政府「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懶政思維。 土地供應諮詢,又稱土地大辯論,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首長林鄭月娥政府所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所推動的一項的公眾參與活動,旨在檢視香港土地供應的來源。
伍美琴2015年榮獲歐洲規劃學界最高殊榮的論文—— 《從香港到台北,探究知識份子在空間使用及市區重建的角色》,正是透過比較台灣寶藏巖和香港嘉咸街重建個案,引證如果建制內外的知識份子願意放下對立、衷誠合作,就可以改變社會的結論。 《香港01》亦多次強調,香港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敢於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把土地資源向市民傾斜的政治家。 雖然,李家超的「天秤」最終會傾向哪邊仍然未知,但若他決定撤回建屋大計,便需要有一個充分理由去說服曾經被他形容為正在水深火熱的不適切居所住戶,為何只能望着只供不足3000會員享用的偌大土地,不能撥出9公頃來建屋了。 第三,高球會2021 年的年度報告書清楚列明, 該會2020 年向特區政府繳付總計903.9 萬元差餉及地稅,2021 年繳付總計811.6 萬元的差餉及地稅。 因此,認為有關哥球會每年只付1000 元租金的陳述具有極強誤導性。 必須承認,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香港逾半世紀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會公平和公正為代價的。
土地大辯論: 小薯茶水間三隧分流 過海隧道新收費懶人包!8.2起率先試行「633 方案」︰紅隧、東隧劃一收$30!年底按時段收費超複雜?即睇詳情!
事實上,早於2017年5月港府公布邀請房協的時候,經民聯的商界議員林健鋒就曾表示郊野公園佔全港總面積約四成之多,故此同意應該檢視能否在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的邊陲地帶發展房屋。 當時則有其他立法會議員斥責此舉等同放棄保育生態價值較低的用地,或者要求官員先做好郊野公園以外土地規劃改建房屋的工作,甚至質疑邀請非政府機構自費研究土地政策違反了法律程序。 只要能大規模的填海造地,投資者便不敢再囤積居奇,如果「發展郊野公園」或「發展農地」不順利,政府不如乾脆集中填海。 盡早填海,三數年已可見成效,原本被「封印」的土地亦會迅間被「解封」。
例如專責小組根據政府的《2030+規劃遠景策略》,指香港長遠欠缺1,200公頃土地,但專家組質疑,香港需要的土地其實不需要1,200公頃那麼多。 又例如,專責小組希望凝聚共識,積極開發土地,但這種重開發、輕規劃的思維,令伍美琴反感。 當時文件列出多個技術局限,包括需要興建額外水務設施、發展新市鎮難解決交通問題等,鄒廣榮卻認為,「技術性問題不難解決,但可能在法律及政治層面上耗費大量資源。」他指出船灣淡水湖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如果發展需要引來司法覆核,在這個層面而言,將會是很大的挑戰。
土地大辯論: 林鄭時代土地大辯論 高球場土地建屋屬選項
”在黑龙江省绥棱县长山镇,众鑫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丛树海告诉记者,近几年合作社添置了不少大马力农机,秋收效率大幅度提升,秋整地也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和更高的作业水平。 土地大辯論2023 「多了地去建私樓,跟人們就不輪候公屋去買私樓,我覺得還有一大段距離。」李美華反駁指,私樓樓價即使回復十年前的水平,即新界400多呎的單位索價400多萬港元,以一般公屋居民的財政能力,仍然是難以負擔。 “目前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农安万亩示范区的核心展示区! 大家看,这片地用的是秸秆覆盖条带耕作技术,不仅保护了土壤,更实现了节本增效。 ”活动中,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梁爱珍介绍了我市“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的实施情况,并重点从秸秆还田、节肥增效、轮作轮耕、区域适宜性等方面展开讲解,以带动各项黑土地保护技术实现大面积推广。
土地小組設立的宗旨主要在於收集民意,並非在社會上引發相關的「辯論」。 「辯論」是一種爭論方式,參與其事者的兩方各據立場,互出奇謀,目的在分辨彼此觀點的正誤優劣。 因此辯論中充滿正與反、是與非、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爭議,並無中間落墨的大團圓結局。 自從土地小組高舉「土地大辯論」的旗幟以來,不論個人或者團體,都可能受到「土地大辯論」口號的影響,大多以辯論的方式爭論土地供應的問題。 土地大辯論 土地大辯論 結果言人人殊,各執己見,枝節橫生,與凝聚社會共識的原意背道而馳。 與此同時,民間不同團體亦提出「反規劃」,以「民間方案」取代政府計劃,當年環保團體環保觸覺指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範圍旁邊,有幅員遼闊的粉嶺高球場,提出收回球場建屋,建屋量可等同整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土地大辯論: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地點
畢竟高球場土地終極用途是政治決定,隨着司法覆核及可預期陸有來的法律挑戰,2029年在原高球場土地上有公屋單位建成的可能性大減,增加短期供應的目標變得遙不可及,那時,再向這個有逾百年歷史的球場「開刀」,理據又是否充分也就易受質疑。 在公眾參與階段,專責小組推出的土地供選項問卷,問卷問題的設計誤導及有前設,被譏諷為似酒樓的點心紙,受民主派議員猛烈批評[37][45]。 土地大辯論2023 土地大辯論2023 建制派也有人不滿問卷的設計,新民黨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的葉劉淑儀更在記者會上怒撕問卷表達不滿[46]。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亦指點心紙式問卷是操作錯誤,惟專責小組主席黄遠輝表示不認同[47]。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亦指點心紙式問卷是操作錯誤,惟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不認同[47]。
- 只要大量填海,越填越多,筆者估計,連環保團體的聲音也會越來越鬆散。
-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雖然被譽為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但幾大本地發展商都形成了自然的寡頭壟斷,駸駸然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
- 「辯論」是一種爭論方式,參與其事者的兩方各據立場,互出奇謀,目的在分辨彼此觀點的正誤優劣。
- 「我們不缺乏土地,我們缺乏對新界土地有長遠、有願景的規劃。」伍美琴解釋,過去香港城市發展主要集中在九龍及港島,但佔地88.5%的新界卻沒有好好規劃,埋下今日土地不足的惡果。
- 現時,很多方法如發展棕地、綠化帶、農地和高爾夫球場建屋等,都會增加地區發展密度,令城市更擠逼,同時又須找地方重置本身的作業使用者,引發不同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住屋是社會需要,不分種族、背景、年齡、性別,人人都有居住合乎人道標準房屋的權利。 因此,上述「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公屋與私樓」、「基層與中產」的二元對立並無存在的理據和必要。 她又為哥球會「平反」,指哥球會每年繳付1000 元象徵式地租卻只服務本地的權貴人士的批評,與事實不相符。 第一,香港早於1969 年推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目的為推動本港體育發展,並吸引海外行政和專業人士來港,加強香港對國際商界的吸引力。 因為特區政府認為批准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符合公共利益,所以只收取象徵式1000元年租。
土地大辯論: 重置棕地繁瑣 填海最具效益 1
本港尚未發展的棕地多達760公頃,相等於40個維園,如果能用作起樓,能供應的單位大增,但當中仍有不少問題未解決。 本星期一(6月7日),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出席環境諮詢委員會後接受傳媒訪問,指出2018年該小組「土地大辯論」的報告顯示主流民意並未支持郊野公園邊陲建屋,因此相關方案優先次序排在較後位置。 剛好在同一天,經民聯又發佈了《香港十年建屋計劃》建議書,提倡先在元朗大欖及沙田水泉澳兩個試點開發郊野公園邊陲提供40多公頃的土地建屋,長遠再把郊野公園總面積的3%即約1,329公頃土地改劃成住宅用地。 現時,很多方法如發展棕地、綠化帶、農地和高爾夫球場建屋等,都會增加地區發展密度,令城市更擠逼,同時又須找地方重置本身的作業使用者,引發不同的社會問題。 土地大辯論 此外,在現時的地理限制下,我們在保護郊野公園的同時,通過填海開發土地是無可避免的。 填海的最大好處是我們可在一大片新的土地由零規劃,有更大彈性和空間平衡住屋及經濟發展的需要。
按此推論,港人若不想住得這麼貴、這麼細、這麼擠,很難避免徵用大自然的資源,亦即是說,很難有無痛的選擇。 不過,多了土地,發展空間增大,市民不用耗費太多的收入在房屋之上,那麼社會便有較多的資源去改善環境,保育工夫可能做得更好。 逃避發展的結果,便是埋下了棕地擴張的伏線,至1983年的「生發案」,更是新界發展的轉捩點。 不過,小組可以怎樣平衡利益群體,凝聚社會共識,繼而選取最能夠惠及大多數香港人的土地供應方案,仍然是個未知數。 《香港01》早前曾經根據小組文件整合有關選項,並參考各個發展區的發展比例,計算可建單位總量。
土地大辯論: 「土地大辯論」的二元對立困局
土地小組用心良苦,但以全民辯論的方式處理複雜的土地問題,顯然並非良策。 我認為棕地使用效率偏低,應該全部發展,但總面積仍遠遠不夠香港需要,而且也要為使用棕地的營運商另外再提供土地,幫助有限。 但不論農地還是棕地,都有產權問題,政府雖可用「收回土地條例」,但若不作出足夠補償,容易被人司法挑戰,戴上強搶民產的帽子,打官司曠日持久,可能要十年八年以上,勝敗難料。
- 「增加土地供應」明明是香港政府的責任,如今竟把問題拋出來讓市民「大辯論」,更突顯了香港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特色。
- 據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立之初,政府只提供至2046年土地供應為3600公頃、需求為4800公頃的兩組數字。
- 與此同時,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推出「土地大辯論」,並應民間要求,將粉嶺高球場納為拓地選項之一,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考慮。
- 然而,2000至2015年間填海造地則只有690公頃,平均每年僅40多公頃。
- 土地和房屋並非簡單的零和遊戲,你有我無;而是開發和分配的合理安排。
雖然棕地發展難,但小組認為難也要做,以確保未來有大規模的地皮供應。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指短中期(現在至2026年)土地短缺情況尤為嚴峻,建議3個土地供應優先選項,包括棕地發展、利用私人新界農地儲備、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 3者可說是未來8年短中期的土地供應希望所在,惟總計只能提供320公頃土地,實際的土地缺口卻高達815公頃,尚欠近500公頃,而且有委員分析,這3個選項各自存在挑戰。 「填海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又會造成無法逆轉的破壞,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規劃、了解和諮詢呢?」作為環保團體一員,李美華非常關注填海對環境的影響。
土地大辯論: 三隧分流 過海隧道新收費懶人包!8.2起率先試行「633 方案」︰紅隧、東隧劃一收$30!年底按時段收費超複雜?即睇詳情! 新文章
碼頭位於葵涌、青衣及昂船洲,由5個私人營辦商營運,佔地279公頃。 一名小組成員以造價約169億元的港鐵南港島線為例解說,稱當時政府指該條鐵路一定蝕錢,因為人流不足,內部回報率低,但其實沒有計及鐵路所創造的土地價值,通車後沿線鴨脷洲利南道住宅地皮的拍賣價168億,已幾乎等於該鐵鐵路的建造價。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政府如欲保住粉嶺高爾夫球場,必須使5個月公眾諮詢得出令中低階層信服的方案,否則,粉嶺高爾夫球場很可能不得不改建公營房屋。 土地大辯論 首先,要立場鮮明,引導香港社會各界明白,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到了必須革新政策思維、採取大動作來解決的十字路口。 至1990年代初政府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原計劃將《條例》引入新界,但遭鄉事派反對,故僅把《條例》適用範疇擴展至已獲「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地區而非「分區計劃大綱圖」,令棕地變得更加「無王管」。 「我們不缺乏土地,我們缺乏對新界土地有長遠、有願景的規劃。」伍美琴解釋,過去香港城市發展主要集中在九龍及港島,但佔地88.5%的新界卻沒有好好規劃,埋下今日土地不足的惡果。
土地大辯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她聲言,很多反對人士認為,高球並非「權貴獨享之物」,但大眾卻將問題歸結為權貴人士與弱勢社群之爭,對高球愛好者極其不公平。 儼如特首「內閣」的行政會議,16名非官守成員當中,一半即8人均申報為香港哥球會會員,當中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湯家驊和劉業強已表明反對收回高球場土地,其他成員包括林健鋒、任志剛、鄭慕智、梁高美懿和陳清霞。 土地大辯論 政府其後提出高密度發展,在收回32 公頃土地中,將北面9.5公頃土地建1.2萬伙公營房屋單位,但在環評及城規會成功闖關後,卻面對香港哥爾夫球會的司法覆核挑戰。 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32公頃土地,因香港哥爾夫球會入稟司法覆核環境評估報告,令建屋大計出現新變數。
此外,他們尚可以指責你們的討論以偏蓋全、不公道或沒有代表性等等。 回歸後,以這麼多年的經驗來說,筆者從來沒見過「大辯論」可解決什麼,最終只會使社會更撕裂。 「其實政府是否也應該有一個更加明確的發展藍圖?對我來說,我是香港人,感覺上這麼多年,都不知道政府想帶領香港到甚麼位置。」對談去到尾聲,李美華提出,政府經常強調競爭力,但從未清晰交待未來願景,包括人口結構及發展什麼工業。
土地大辯論: 增加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發展密度
再者,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本港貨運物流業發展蓬勃,但政府物流產業配套不周,沒有規劃足夠用地,在貨櫃用地需求激增的情況下,新界面貌急劇轉變。 根據本土研究社《棕跡——香港棕土政策研究報告2015》,在1983年至1993年間,位於新界的港口後勤及露天存貨用地,由276公頃倍增至560公頃;往後20年間,新界棕地不斷擴張,至2015年的棕地面積已多達1,192公頃。 發展局提交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文件也估計,目前本港有約1,300公頃棕地。 談到小組的工作挑戰,鄒廣榮指現時委員仍未就土地短缺數字有共識。 當初政府討論未來香港土地需求時,援引《2030+:跨越2030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當中提到未來香港長期需要4,800公頃土地,撇除已落實規劃的3,600公頃用地,現時尚欠1,200公頃。
傳媒方面,香港01等主張收回球場建屋[38],星島日報和東周刊主張保留球場[39][40],成報則認為爭議非零和遊戲[41],並且要考慮遷移過百萬市民到新界北居住的配套和交通負荷[42]。 其次,特區政府和土地專責小組還應當爭取中央支持,幫助特區協調大地產商與普通居民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群體與中低階層居民之間的矛盾。 香港需要高爾夫運動,成功人士應當在香港有地方打高爾夫,但是,何者為「大」? 「小組本身由不同的利益團體組成,還要面對社會不同持份者,相當困難。」黃澤恩笑言,小組工作性質之複雜及工作量之龐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幾乎要「全職」參與這份「義工」。